
7月最熱的那幾天,我一個人關在外地租來的屋子裡淚流滿面,一個是我深愛的媳婦,一個是我最好的朋友,他們卻在我背後深深地捅了我一刀,這種痛是痛在骨頭裡,讓人幾乎要發瘋!
我不顧一切又跑回了濟南,在第一時間找到了正在上班的卿雲,她辦公室裡的同事從來沒見過我那樣失控,一個個瞠目結舌!只有卿雲面色發白,還比較鎮靜。到家後,我彭地摔上門,沖卿雲咆哮起來“我哪裡對不起你?你就算要紅杏出牆,為什麼是黑信?”
等我怒吼完,卿雲才開始講他們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了一起。卿雲說“有一次,他把車子開到單位樓下,如果我不上他的車,他就要衝所有人大喊我是他的情人!我怕事情鬧大了,就上了他的車,後來他就一直拿這個來威脅我……”
我聽得雙拳攥得咯咯作響,啪地給了自己一耳光,又啪地給了卿雲一耳光,我恨自己引狼入室,我更氣惱卿雲的軟弱糊塗!我啞著嗓子問卿雲“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?”卿雲哭著說“我沒臉說出來!”她又說“是我傷害了你,我會以死彌補自己的過錯!”
這是卿雲第一次提到“死”字,我聽了心裡打了個寒戰,卻狂躁地吼著“死有什麼用?都是那畜生,我要宰了那畜生!”然後不顧卿雲的阻攔摔門出去找黑信,背後是卿雲撕心裂肺的哭喊。到了黑信住處,他早就聞風逃走了。
就在今年年初,他已經和他媳婦離婚,他住的公寓裡鐵將軍把門,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。我給他打手機,他倒是接了,他說“哥,我這輩子都沒臉見你了!我是真心愛嫂子,這麼多年,我沒有一天不拿嫂子和我媳婦作對比,那是一個天上,一個地下啊!和嫂子發生那種事都是我一手預謀的,你不要怪嫂子,她心裡裝的人只有你一個!”
掛上手機,我一個人在大街上遊走到深夜,然後像具木偶一樣立在遠處,眺望著曾經屬於我的家,家裡的那盞燈一直亮在那裡,我徘徊了又徘徊,等我步履蹣跚地回到家裡,才發現卿雲把家裡所有的安眠藥都吃了!
總算是不幸中的萬幸,經過急救,卿雲的性命好歹保住了,現在身體正在慢慢恢復,可是比起身體的創傷,情感上的創傷要難以癒合得多。從醫院回來後,卿雲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,什麼話也不說,臉色蒼白得像紙。我對她說“我已經放下了,你也要放下所有的包袱,咱們再重新開始一切!”
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,這個包袱要怎麼才能放下呢?把卿雲送到醫院急救的那天晚上,我在急救室外又一次給黑信打電話,我說“你這個畜生,你不但傷害了我,你還傷害了兩個家庭!卿雲要是有個什麼意外,你就是逃到天邊,我也要宰了你!”黑信說“我知道我錯了,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……”
為了不讓事態擴大,影響卿雲的名聲,我讓卿雲隨我一起去外地呆一段時間,卿雲堅決不去,而且一句解釋的話也沒有,我的情緒又有些波動,我說“就算是我錯了,你一定要以折磨你自己來折磨我嗎?”卿雲還是不說話,只是對著窗外的知了叫聲出神。最後還是我一個人去了外地,但心卻留在了濟南。
七夕那天晚上,我買了一大束玫瑰花回去看卿雲,她見了勉強地笑了笑,兩個人之間像陌生人一樣不自然,這讓我特別痛苦。


 糯米香酥條
糯米香酥條 三絲拌銀針粉
三絲拌銀針粉 瓜子酥的做法
瓜子酥的做法 水煮牛肉的做法
水煮牛肉的做法 北京小吃--驢打滾
北京小吃--驢打滾 北極甜蝦豆皮煎
北極甜蝦豆皮煎 洋芋擦擦的做法
洋芋擦擦的做法 芸豆冬筍燜仔排
芸豆冬筍燜仔排

 石榴才真正是女人的紅寶石
石榴才真正是女人的紅寶石 8招幫你甩掉最後十斤肥肉
8招幫你甩掉最後十斤肥肉 常吃20種食物 美女變成大媽
常吃20種食物 美女變成大媽 10個健康殺手最傷女人
10個健康殺手最傷女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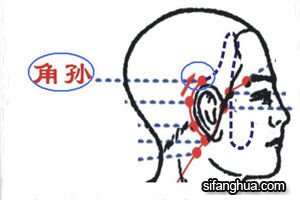
 酸辣蘿蔔脆
酸辣蘿蔔脆 豆豉烤魚
豆豉烤魚 檸汁茶香排骨
檸汁茶香排骨 香脆黃瓜丁
香脆黃瓜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