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個泥瓦工,我家裝修時,由我哥帶來的。第一次見到他,是盛夏,他穿一件紅背心,20多歲,下身是那種很便宜的沙灘褲。不知為什麼,我一下子就被他震住了,他的眼神是那麼“鋒利”,他的眉手是那麼濃密,更要命的是他有胸毛,讓人禁不住聯想他胸口的毛怎樣延伸開來,那一定是條美麗的小路,我想像著,美化著它,竟感覺到一些詩意。
可轉念,我就想入非非起來,我喜歡這樣,那是一種心跳的感覺,並且全身酥軟,然後是無邊的汪洋把我托起……
那是一個早上,全家人都不在。我正在洗手間裡,他突然提著工具進來了,我來不及站起來,多次想入非非的一幕就終於出現。不知是有意還是慌亂,我站起來時,褲子竟沒有提,他呆立了片刻,然後是緊張地靠過來,那一刻,如果我推開他,或哪怕只是作秀地說個“不”字,他一定會退出去,可沒有,我鬼使神差地迎了上去,發抖,氣喘,任他撫摸……
他真是大膽,讓人想不明白。也許是平常我用變形的表情暗示了他-或者青年男女在一起是敏感的,甚至神經質的-或者我弱智的形體語言,暴露了我內心的掙扎和企盼-總之,我與他的第一次正面交流,居然是這樣一種原始狂野的方式,一切盡在兩具滾燙的身體間吐納與交融。
原來,這樣的感覺如此舒服。原來,身體不是籠子,是向陽的葉子,是迎蝶的花朵,他是那麼兇猛如火如荼,我需要燃燒,所以緊緊地回應著他,像是一種本能。他一直摟著我,一直站著。兩束昂立的火焰,相互摩擦著。我渴望躺下,然後看他氣吞山河地撲下來,可是,他霸道地扶著我,勃發的下體猛烈地撞擊著,他的眼睛血紅血紅,像是要殺人……我顫抖著,感覺天暈地轉,我想喊。突然,我聽到了有人上樓的聲音,是媽媽買菜回來了。
他剎車,緊急放下我,然後奪門而出,跑到客廳裡,裝模作樣地敲打著,我忙整理衣裝亂髮,面紅耳赤地回到自己的臥室,關上門,趴在床上,心有餘悸……還好,還好,那只是表面接觸與撫弄。臨鏡梳妝的那一刻,我突然驚醒,怎麼可以這樣-我有些後怕,同時又暗自慶幸,剛剛發生的一切好在還只是“表面文章”,我要做聖潔的處女,直至洞房花燭夜,這是家族的要求與期待,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啊。可是,早晨的瘋狂,竟差點兒斷送了我25年的堅持與驕傲。


 糯米香酥條
糯米香酥條 三絲拌銀針粉
三絲拌銀針粉 瓜子酥的做法
瓜子酥的做法 水煮牛肉的做法
水煮牛肉的做法 北京小吃--驢打滾
北京小吃--驢打滾 北極甜蝦豆皮煎
北極甜蝦豆皮煎 洋芋擦擦的做法
洋芋擦擦的做法 芸豆冬筍燜仔排
芸豆冬筍燜仔排

 石榴才真正是女人的紅寶石
石榴才真正是女人的紅寶石 8招幫你甩掉最後十斤肥肉
8招幫你甩掉最後十斤肥肉 常吃20種食物 美女變成大媽
常吃20種食物 美女變成大媽 10個健康殺手最傷女人
10個健康殺手最傷女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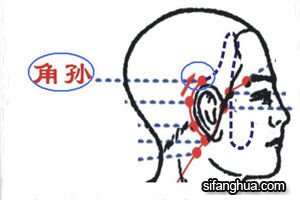
 酸辣蘿蔔脆
酸辣蘿蔔脆 豆豉烤魚
豆豉烤魚 檸汁茶香排骨
檸汁茶香排骨 香脆黃瓜丁
香脆黃瓜丁